【书香祥云】村庄忆旧
点击标题下
祥云时讯
即可订阅
村庄忆旧
朗读者:夏霁荷
夏霁荷,19岁,现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喜欢旅行和摄影,阅读与电影。人生的目标,在于向前,也在于拐弯。人生的成长,在于学习,也在于经历。
大约去年6月上旬,著名散文家王剑冰先生来到了云南驿,写下了一篇赞誉云南驿的文章。当时,他对云南驿是这样描述的:
“我走进一个有着三四进房屋的更大的院落,下面有马厩、接待室、厨房之类,上面是讲究的住室。几十个人住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从木板墙上遗留的字迹可以看出,这里的每一间屋子,都曾传出过朗朗的书声。很多有特色的豪宅大院都是被当做学校留下来的。这里到处堆放着驿站的遗迹,失去光泽的老茶,固定的马驮子,硬皮子的马靴,成串的马掌子钉在墙上,钉出了一个茶马古道的线路图。我轻轻摇动了圣果样的马铃,它发出的声音超出了我的想象,那本该叮叮向上的声音,却橐橐沉远。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声音,它和茶马古道的石板声形成了互应。还有马灯,那微小的亮光,是夜路上的另一种声音,加上马发出的声音,人偶尔发出的声音,就构成了浩浩孤旅上的生命交响。”
多年以来,无论是来自我们本地的,还是来自远方的游客,面对着曾经一度繁华的古老驿站,现在如此落寞,都会发出内心的赞叹。不管是目不识丁的乡民,还是开化的、来自现代文明都市的旅人,面对云南驿曾经的磨难、战火和烽烟,面对这英雄的栖息之地,面对云南驿的膜拜和感伤,却都是一样的。人们面对云南驿如此苦难的历程,每每感到惶惶然而不知所措。因为,云南驿,它存在于众多的马帮出行的某一个驿站,也可以存在于众多的军事航空站中的某一个毫不显眼的角落。然而,我们面对的云南驿,它曾经承载的让人无以复加的悲壮和记忆,和今天的寂寥和默默无闻,往往让我无法准确的说出什么来……
这就是今天的云南驿。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它已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了两千多年了。云南驿在晨光中,永远是金黄的。金黄的古道、屋顶、马帮、驿站,连饮马石也被折射得分外耀眼,朝着人们的视线,游离开了,飘向那高远的天空。天空永远蔚蓝,白云们偎依着,飘来飘去,灰色的瓦顶上,枯草微微摇着头,仿佛从遥远的汉唐一直守望到今天一样。远处飞来的阵阵鸽群,在古老的屋顶上空盘旋着,哨声悠扬而清脆。古道边,透过门的间隙,可以看见玫瑰、月季、兰花在庭院里寂静地开放。在傍晚即将来临的时候,人们似乎都放慢了脚步,悠闲地享受着岁月恩赐的安逸和幸福。而夕照下的云南驿,则有更加催人归家的感觉。
展开全文
古道两旁,一爿爿马店,敞开着大门,迎进南来北往的马帮。此刻的云南驿,显得雍容、繁忙。它敞开着胸怀,包容着南北商帮,吸纳着他们的习惯、汗臭。马锅头们在卸下马驮后,悠闲地抽上一支烟筒,洗上一个徒弟们伺候的热水脚,把当晚夜宿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吹着口哨,出马店大门而去。他们有的到老朋友家叙旧去了,有的去酒肆喝酒、赌钱去了,有的找当地相好的女人去了。这是明末清初直到上世纪初的某一个黄昏的云南驿,就在那个被当代艺术家描摹的黄昏,无数队马帮,从遥远的地方,都汇聚在云南驿,然后在第二个清晨,又匆匆离开了它,向着更遥远的地方跋涉。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写不尽游子天涯孤旅的愁绪。当有一天,我发现了云南驿正以自己的姿态,在彩云之乡那古老的天空下,等待了我们两千多年的时候,我们来的才真正的晚了。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的马帮文化。只要你在云南驿,就能找到心灵的慰藉。温暖的火塘,热腾腾的烤茶,喧嚣的酒肆,仿佛使你回到上个世纪初期的云南驿,回到那个汉唐烽烟弥漫的古云南……
这里曾经来了徐霞客,来了吴三桂,来了岑毓英,来了林则徐,来了飞虎队和陈纳德……是云南驿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也是他们把云南驿带到更加宽广的世界。
作者简介
麦田,原名普元玺,笔名麦田,现在祥云县文联工作。作品刊登于《诗刊》《大家》《创世纪》《边疆文学》《绿风》等,出版诗集《妈妈在天上看我》《南行记》《云与南》。曾获滇西文学奖、大理州首届文艺创作诗歌奖。
祥云《法律大讲堂》第十三期
图文发布 县融媒体中心
责任编辑 杨仕宇
图文审核 张敏来
图文总审 胡林果
讲好祥云故事 传播祥云声音
祥云时讯 与你同行
投稿邮箱 3109820189@qq.com
媒体地址 龙溪小区308号(县融媒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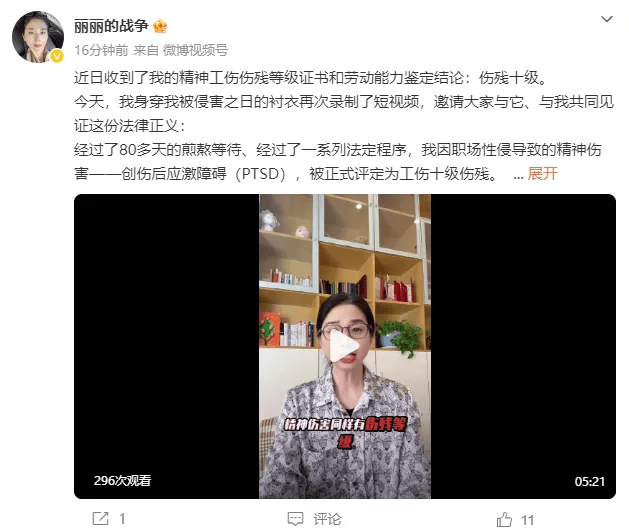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