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此文寻找失去联系多年的曾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回忆二哥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进入北方一所大学读书。入学伊始,寝室中的九筹好汉序齿以定座次,二哥行二,我行五。说实在的,“二哥”这个称谓在我们中间的利用率并不高,较多的时候称之为“老二”,不忿的时候则称之为“二饼”、“横路敬”。
那人中等身材,紫黑脸色,面颊瘦削,胡茬浓密,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却是不折不扣的双眼皮,再配上一副近视镜和粗硬、不羁的头发,便居然有了几分英气。他常年穿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上身笔挺,风纪扣紧扣,下身裤管粗圆,似非大雅,这主要缘于他走路时的步态。他有点外八字,走起路来多少有点蒙古跤手捕捉战机时的味道。二哥来自该省北部的一个小城,岳飞信誓旦旦要捣的黄龙府就是这里。
二哥是个认真的人,在学习上异常努力,只要有闲暇,总是安坐在自习室里。我喜欢借看他的笔记,字虽然极差,小如蚊蚋,扭曲如飞天,但却一笔不苟,本面整洁。开设《植物解剖学》的时候,任课老师对绘植物图有一种几乎病态的偏好,我们动辄要盯着显微镜花费几小时来完成作业,我天生不好此道,大作难入老师法眼,而二哥却乐此不疲,边画边哼哼,竟然频频得优,这让我又恨又妒。
虽然用功,二哥的考试成绩却一般,他是我接触过的同学中应试能力最缺乏的一个,往往是在复习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分数却不高。英语尤其是他的弱项。每次下定决心学外语,把一本单词书的前几页写得密密麻麻,大约个把星期过后,本轮攻击无告而终,再隔上个把月,此过程周而复始,重新复习前几页单词。
现在想起来,二哥的长处和短处一目了然,他长于应对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短于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记得在每次大扫除的时候,二哥都要对日光灯大动手术,拆下来分解成零部件,擦拭后重新装上,居然每次都亮,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可惜日光灯并不需要天天擦拭,对二哥的个人崇拜并没有形成,更多的时候,二哥的短处显漏无遗。有一次寝室里商量出联欢会节目,老九的一个创意是每人唱一句与动物有关的歌,然后再学一声动物叫,如“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然后伴着一声“哞……”,大家纷纷自报歌曲,二哥一语惊人:“我学人叫!”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哪里不对,老七聪明地引申到:“二哥说要学人叫,就说明他承认自己不是人。”话音未落,已被扑翻在床上,大家绝倒。
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罗大佑在我们中间很有市场,再后来就是童安格、王杰、李春波等。二哥雅好音乐,尤喜流行歌曲,但因音质、音色的关系,唱功一直未臻上乘,聊为自娱而已。有一次二哥在阶梯教室里头戴耳机、憋细了嗓子学唱孟庭苇的歌曲,不觉忘情,声音渐渐地大了起来,我们几个挤眉弄眼示意不要惊动他,果然,二哥很快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摇头晃脑制造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低徊处宛如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高昂处宛如木棒猝然间击中了狼的后腿。全年级同学先是愕然,继而惊恐,最后是皆大欢喜。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次,那是在全班排练大合唱的时候,我指挥其他同学集体失声,效果也不错。
在大一的上学期,有一个颇有些才气的女生主动接近我,慢慢地我对她产生了好感,不久以后她又倏忽间远离了我,当时让我不少次地临风流泪,对月抒怀。这一过程又在别人身上重复了几次,我发现规律了:她就像狗熊掰苞米一样执着地寻找着她的爱情,掰下一个,端详一下品相,然后继续往前走。这一次,她选定的苞米是二哥,就这样,我和二哥成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同情兄”。
我们密切关注着二哥的感情进展。果然,有一天我晚自修回来后,发现二哥躺在床上,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天花板,看来二哥还是没有能力打破这个怪圈,那是在元旦前夕。没有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永远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元旦所带给我们的欢乐,我的大学生活中大部分美好的记忆是围绕着元旦展开的。大概在此前的半个月,我们的心就开始因激动而颤栗。班级先要开会,然后几个小组分头行动,去批发贺年片,去买面、油、肉馅,去买气球、彩带,去装饰教室,去准备、统计联欢节目。到了元旦那天,先是中午的会餐,时间要持续到傍晚,稍事休息后是晚上的联欢会。午夜的钟声敲响后,开始包饺子,然后拿到食堂煮,踏着积雪,在鞭炮声中脚步轻盈地往返……举目所极是气球、彩带和笑脸,俯身是水果和点心……直到如今我还记得一封动员信上的几句话:“……时间: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一个不醉不归的夜晚;人员:清一色的兄弟姐妹……”
然而这一次,所有的欢乐都不属于二哥。他那痛苦的样子让我们揪心,我们所有的劝慰、指正、训斥对他都不起作用,他的人生目的变得直接而单一,至少是在这一时期。转过年的春天是早春植物实习,我们正围着老师和标本“问,闻,望,切”,女孩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二哥像行吟于泽畔的屈大夫一样孤零零地在远处的一个山坡上逡巡。二哥是个过分认真的人。
转眼到了暑期的考试前夕,大家埋头复习。复习中有很多窍门,比如说同一道题目如果大家多次去问老师的话,老师不胜其烦就会有意无意地透漏出一些观点:“这道题随便看看就行了”,“这道题要会做……”等等。同学之间再一交流,就基本上每人都整理出一份应试的“葵花宝典”,宝典中大概能涵盖百分之六十的题目。当然没有人会傻到把宝典与其他人共享。鉴于二哥因情感磨难而无心复习,我慨然把宝典借给二哥使用。再后来,我在那个女孩的手里看到了宝典的复印件。
这段感情持续到下一年的元旦前夕才暂时画上了句号。
大四的上学期,我和老六、老七、老九埋头准备研究生考试,二哥虽然久有志于此,却因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未通过系里自定的报名资格审查,这样一下子空闲了许多。在失落了一段后二哥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原因是他和那个女孩分到同一个毕业论文实验小组,共同的学习和生活(姑且这么认为)使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事态的发展我们一开始也看不懂,二哥也神神秘秘地,但后来结果明朗了,女孩再一次勇敢地说“不”。转过年来考研成绩发布,我们四个顺利通过。毕业前的那段时间大家空闲得要命,二哥在找工作之余常常穿戴齐整地到一个曾带他教育实习的年轻女老师那里看书,这让我们猜测了很久。
二哥的工作分配不太顺利,一开始希望能留在H市,在多方活动无果后,他的去向只有两个:一是回老家教书,一是到一个大型国企的职工培训部去,二哥选择了后者。后者的好处显而易见,那时人民教师的称号远没有现在辉煌,教师即使把工资全部换成零钱,腰包也不会比现在鼓多少。但后者的弊处也不少:地点太偏了,位于“黄龙府”的一个镇上,而且我觉得二哥也不适合去人际关系更复杂的国企工作。二哥自己也不满意,他曾感慨地对我说:“五弟,我是咱班分得最差的。”他指的是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地点是在镇一级行政单位。
毕业的时间渐渐近了,即将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集体和同学,孤身赴陌生的环境,应对陌生的人和事,想起来就感到恐慌。大家互赠照片,写留言册,惜别的情绪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每天不论起得多早,在校园的小路上、树丛边总会看到三三两两要好的同学在谈心。
分手来得很突然。毕业会早已开过,行李也已经寄走。我们把同学一一送走以后仍然不想回家。宿管科多次勒令我们离开,我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中午得到通知,当天晚上所有的毕业生宿舍就要换锁,大家纷纷从床上跳下来,匆匆告别后作鸟兽散。
研究生生活并不像想象得那样美妙,最难以忍受的是孤独和封闭。白天忙于上课,应对导师,晚上在狭小的实验室里忙应接不暇的作业和实验近午夜,“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书桌上方悬挂的就是寝室的合影,看见它,我的心中会忽然一动:不知二哥现在怎样了。
毕业后的第三个月,二哥找机会陪同事来H市出差,约我和几个同学去见面。我们到时候,二哥正在一家化工厂的大院里兢兢业业地擦洗一部面包车,同事大概上去办交涉了。看到他那股认真劲,我们几个颇有感慨:三个月的工作经历使二哥乖巧多了。转过年来二哥又来到 H市和我们会合,一起去参加一位同学的婚礼。从那以后只要有同学结婚二哥必来,婚礼结束后就回到学校住一晚,微醺以后是必不可少的卧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某一次聚会,元旦联欢,野外实习……有一次二哥执意要我们陪他回原来的寝室看看,那里已经住进了外系的女生,二哥进去后在他原来的床位前站了片刻,在女生们诧异的目光中匆匆退出。我能体会到二哥的孤独、落寞,我心里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觉:二哥大概是同学中最留恋大学生活的人,在他心中我们大概是最能包容他也最能理解他的人,参加同学的婚礼大概是他回味大学生活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老大是男生中第一个结婚的,那是毕业后第二年的初春,我们提前一天会集到了H市近郊的那个小城,就落脚在老三家里,老三和老大分在一个城市。然而直到婚礼结束二哥却迟迟未到,当前晚上,大家酒酣耳热正在折腾老大夫妇,突然接到电话,二哥已到火车站,让我们去接。原来二哥当日凌晨即已出发,本以为可以赶上中午的婚礼仪式,却因修路多绕了7个多小时。
大家轰然而起,涌到火车站。这次二哥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身边立着一个女孩,身材小巧,面目清秀,声音宛如莺啼燕语。当天晚上的具体细节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们非常非常高兴,闹完洞房出来,大街上已是寂静无人,漫天飞雪,一路上大家一遍遍唱着“一剪梅”,在雪光的映照下我分明看见二哥的眼中噙着泪花,那个女孩紧紧抱着他的胳膊。我的脚步慢了下来。
当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晚,打牌、打游戏、看电视,各取所好,在给那个女孩安排好住处以后,二哥先是打了一会儿牌,最后终于支持不住,脱掉鞋,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整个房间弥漫着二哥那久违的、令我倍感亲切的脚臭味道,在这种味道中我感到无比的安宁,无比的欣慰。大概两点钟的时候我终于支持不住,扑到隔壁的一张床上沉沉睡去。睡梦中隐隐听到有人在叫我:“老五,老五”,我勉强半睁开眼,凭感觉是二哥,他拉着我的手道:“五弟,我要赶车去了”。我极力想挣扎起来送行,但只是勉强说出了“二哥再见”几个字后就被睡魔掳了过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问下来知道二哥是三点钟走的。
就在这年的冬天,二哥给我写信通知我召集哥几个去参加他的婚礼,信中的口气异常肯定而坚决,只告诉了事由、时间和地点,指定由我召集。他大概认为我们不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还会像以往一样人员整齐、浩浩荡荡,在他的婚礼上笑骂、纵酒、狂欢,我还想象得出他会如何自豪地向同事、朋友、亲戚介绍他远道而来的铁哥们。就在这一次我做了一生中都不会原谅自己的几件事之一。现在回头想起来,路远(要乘八个小时的长途车),毕业论文紧张,天寒地冻都不是没去参加婚礼的真正原因,大概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二哥那种参加同学婚礼的迫切心情;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多次参加婚礼后已对这种活动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大学生活逐渐远离,它已不再或从来没有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二哥那样。
当我们最终决定不去的时候,发现剩下的时间甚至已不允许我们写信通知他,而且这信也很难写。总之,我们把最后的打击留到了婚礼当天。现在我已能想象出二哥当天从盼望到焦虑,到失望,到愤怒,到悲伤的整个过程。再后来我辗转听到了二哥几次过校门而不入的消息,我知道,这一次,二哥真的伤得很深。
一年多以后,我们已经毕业,那年夏天是老六的婚礼,除了二哥,婚礼当天男生都来了。有两个人就要马上远赴美国和日本,我也要南上求学,研究生宿舍这个同学的中转站和情感枢纽也即将不复存在,大家纷纷娶妻生子,问舍求田,再聚齐的机会几乎没有,大学生活真的要越来越远了。婚礼结束后已是华灯初上,大家依依不舍。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老六坚持要我们到他家里继续喝酒畅谈。当走到离家门口还有几十米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心中一动,难道是二哥?真的是二哥,他灰尘仆仆,坐在台阶上,正在喝一瓶矿泉水。后来我知道,二哥最终还是决定来参加婚礼,中午赶到的时候家里已空无一人,又不知道婚礼的地点,枯坐了几个小时。
进屋后大家坐定,我们一直不敢看二哥。老九举起一杯酒送到二哥面前,没等他开口,二哥接过酒杯,用手指把我们一个个点过去,最后定在我的身上:“你们这几个狗东西!”然后红着眼睛放下了酒杯。
再后面我南上求学,和同学的联系越发稀少,有一次二哥给我写信,说要报考我校的研究生,我打听了一些消息写信过去,却没有了下文,再后来我又听到了二哥生了个小女孩的消息。再后来几年不通音信,二哥的消息已断绝。
偶然读到张抗抗女士的一段文字让我心中有所触动,现摘录如下:
“我才意识到那样温馨的夜晚,在我心中也许都不会再有了。那种青春的友谊,情感的依傍,孤独中的慰藉,那样真诚,彼此无私无求的信任……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能温习而不可重现!”
告别大学生活已经有十几年,最后一次见到二哥距今也有七八年了,梦中和印象中的二哥依然是英迈少年的模样,这倒是意外的收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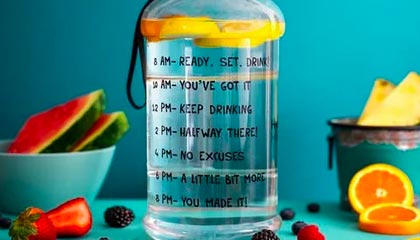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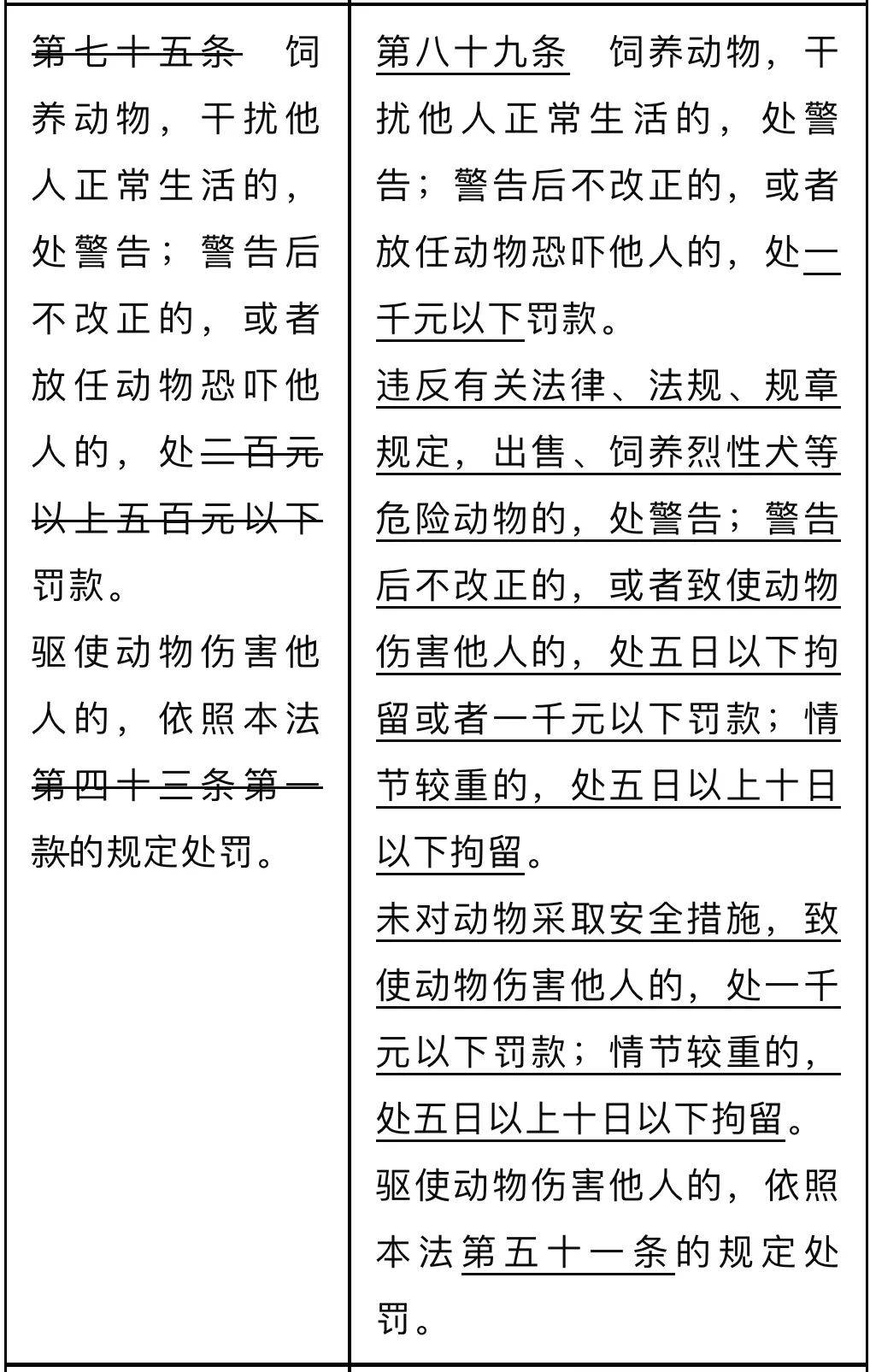


评论